复旦大学:蒋锦桐
“之前在哪里知道的‘中国梦’?”
付秀兰想了想,“应该是从户外屏幕之类的地方吧。”
付秀兰是康城小学六年级学生何胜男的妈妈,当天她与女儿一起来参加“梦想六一”的活动。她说不清“中国梦”是什么,也不觉得自己对未来有什么确切的理想可言——如果有,那也是与其他母亲一般无二的、对子女未来的期望。
1999年女儿何胜男出生后,她就辞掉了原先在制衣厂加工的工作在家照顾孩子。随后第二个女儿、小儿子接连出生,她的作息大体从那时延续到了现在。
五点半起床以后,付秀兰开始为新一天做准备。
“大女儿六点就起。她起得早,能自己骑车去学校;两个小的让他们多睡半个小时。”之后付秀兰要送四年级的二女儿与一年级的小儿子上学,“学校离得不远,我骑电瓶车送他们去。”
看电视、上网,偶尔串串门,收拾下种在还没建起房子的空地上的蔬菜,付秀兰的日程表又到了接孩子下学一项。
“他们下学时间不一样,我得去两趟。”付秀兰不再工作,也与这有关,“小的放学早,我得三点半之前就到。找工作人家没有这么早下班的。”
接孩子放学以后,付秀兰顺路带上晚上做饭的菜。晚餐是一家人交流的好机会。丈夫承包了一只队伍,做室内装潢的生意,有活儿时就非常忙碌;孩子们晚餐以后就要去写作业。在付秀兰看来,丈夫不仅忙,也不太擅长和孩子们交流。
“他爸带孩子,倒不如他们大姐姐。”说起何胜男,付秀兰毫不掩饰对大女儿聪明与懂事的得意,“她成绩好,每年都能拿年级里的奖;弟弟、妹妹学习上有问题,也是她来指导。我们实在帮不上什么忙。”
付秀兰一家睡得很早。他们租的房子有两间卧室,夫妻两人带着小儿子,姐妹俩一间。小儿子困得早,八点半就躺下;姐妹俩九点多写完作业也睡了。“差不多我们也这时候洗洗睡了。”付秀兰说。
每天基本都是这样。付秀兰没有想过两、三年后,当小儿子也自己上下学时,她的一天要如何安排。“刚来上海的日子苦,不知道以后出路在那里。后来有了三个孩子,学费在加上其他,起码要八、九万;现在经济宽裕了,想的也就是孩子,希望以后他们好。”
“我们现在也就春节的时候才回信阳老家,孩子们不愿意回去,住不习惯。”付秀兰一家已经在上海扎下了根,也许几年后她也必须要为孩子们的未来做打算。“我们农村出来没什么文化,就是希望把孩子培养出来,将来能继续留在上海念书、考大学。”虽然现在还没有针对付秀兰一类来沪工作者子女考学资格的具体解决方案,但她还是有期待的,“孩子还小,也许等到几年以后就能解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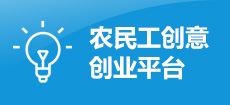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1502003094号
沪公网安备 3101150200309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