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戴心怡
一张木桌紧挨着电线杆,三把塑料椅一字排开,每个星期天,张兴龙都要为小女儿和前来辅导她功课的志愿者在国京路边“布置”“临时教学点”。30米开外,是蓝顶遮雨棚搭成的菜场,叫卖声和不远处工地的打桩声掺在了一块儿。
张家不到十平米的租屋里没有窗子,唯一的光源是木桌上用铁夹固定着的一盏昏黄的灯。“如果能多租一间房子就好了,婧伟就不用坐在路边上课了,屋里总比外头安静些。”在上海卖了十二年大饼、“转光了浦西所有批发市场”的张兴龙一直梦想着能给小女儿一个“好一点的未来”。
2002年春节,33岁的张兴龙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从老家来到上海。由于没有借到房子,张兴龙在火车站的地上铺了一条毯子,一家人轮流看包,度过了在异乡的第一晚。
十年搬了八次家后,如今,张家五口租住在两个窄而霉的房间里。一间月租500元的还没打扫好。所以,用木板隔出的另一间“蜗居”中便塞进了一家子。“350元一个月,不包水电煤”,张兴龙说。连着下了两天的雨,屋内的泥地面上多了几只深浅不一的脚印。
不足千元的房租远低于离棚户区十分钟自行车程的五角场商圈,但仍占了张兴龙月收入的大部分。“做得少,不够房子钱,做得多,人累。”下个月,房租又要往上“爬”了。
“也还是很想买房子的”,可张家饼摊每天至多100来元的利润让这个过了不惑之年的男人觉得“只是个奢望”,“除非等婧伟长大,给我们老夫妻俩买房子!”
11岁的小女儿婧伟来上海8年了,她是张家唯一一个不用每天起早摸黑做饼、卖饼的人。
“只希望她好好读书”,张兴龙满心期盼孩子能留在上海读初中,甚至是升入高中、考大学,“能有一个好一点的未来,将来不用和我们一样辛苦。”但女儿的班主任告诉他,孩子“有90%的可能性要回老家念书”,剩下那10%的希望则是“补交社保”。
做小生意的张兴龙夫妻从没有缴过社会保障金,他算了一笔账:每个月最低700元,交15年,总共12万。根据今年4月公布的《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3年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暂未列入保险范围的外来务工人员,需在就业所在地的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就业服务窗口办妥灵活就业登记,或街道、乡镇开具的从事1年及以上就业证明。”
卖饼的张兴龙开不出就业证明,一位与他相熟、在杨树浦路摆蔬菜摊子的老乡也没有。今年,老乡的两个孙子因无法在上海继续学业,被“送”回了老家。张兴龙愈发强烈地觉得自己的小女儿也将面临同样的结果。“如果回老家读书,只有80多岁的奶奶可以照顾她”,张兴龙实在不放心。
“就算只有10%的希望,我们也抱着90%的期待。”还有一个半月,婧伟就要参加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了。班主任的话和老乡的遭遇,让张兴龙更加焦虑,“走一步看一步吧”。在记者转告《意见》之前,他既不了解具体的政策,也不知道从何了解。
“如果婧伟能留在上海,那么我们一家都不回去了,就安心地住在上海!”张兴龙梦想着小女儿能像她的安徽籍班主任一样,留在上海工作、买房。“希望政府能多关注外来务工者的生活,能多考虑我们这些做小生意的实际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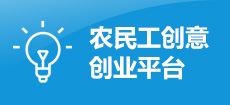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1502003094号
沪公网安备 3101150200309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