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7日,上海市终身教育研究会会长王伯军校长为李经中理事长著的《父母的两个世界:一位60后的深情追忆》撰写书评。王校长曾担任上海开放大学副校长,也是上海市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家宣讲团成员,书评标题为“‘8’件事‘3’个点‘4’道关‘1’生情---《父母的两个世界:一位60后的深情追忆》读后感”,内容如下:
李经中撰写的《父母的两个世界:一位60后的深情追忆》(复旦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吸引我,一方面是因为我也是从农村世界来到城市世界,产生了共鸣。另一方面是因为有意思,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描述,文字生动,可读性强,更有意义;其中的“8341”很有价值,即“8”件事(江汉平原的农村世界)、“3”个点(作者成长过程中的关键点)、“4”道关(从农村进入城市须面对的考验)、“1”生情(作者与父母的深厚感情)。
一、“8”件事(江汉平原的农村世界)
1、除夕。
根据作者家乡江汉平原的习俗,在吃年夜饭之前,要先放鞭炮,然后将猪头肉等贡品摆在祖宗牌位前,祭祀祖宗后才好吃饭。作者父亲和母亲会在除夕前一天晚上,将猪头、猪肝、猪肚、猪腰等菜卤好,猪肝、猪肚等菜可以切出来放在盆子里,供春节期间招待客人用,但猪头不能动,必须是包括猪耳朵和猪舌头在内的完整的猪头,要等供完祖宗后才能分食。
吃完年夜饭,休息一会后,去祖宗的坟地送灯,据说是要用灯照亮祖宗回家的路。到了坟地,要先放鞭炮,然后烧纸钱,焚香祭拜,祈祷祖宗保佑一家人平平安安,子子孙孙兴旺发达。改革开放以来,这送灯与其说是一场祭祀活动,还不如说是一场社交秀。因为都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去送灯,这里能碰见许多多年未见的外出谋生的乡邻。
2、正月。
大年初一天亮之前先在堂屋里放鞭炮,放好鞭炮才能开门,据说这是要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把家里一切不好的东西都请出门,让这些都随风而去。“早晨起来后我们会给父母拜年,父母也会给我们压岁钱。”
然后就是正月十五的晚上了。作者老家没有元宵节这一说,但有“三十的火,十五的灯”的说法,意思是说大年三十和正月十五的晚上都要张灯结彩,基本上只要有电灯的地方,都要把电灯点亮,但在点灯之前,还有一个到地里“赶毛狗”(毛狗就是狐狸)的仪式。这“赶毛狗”的活动名称曾经出现一些变化。因为毛主席姓“毛”,为了避讳,曾经一度将“赶毛狗”称为“赶蒋狗”,当然这里的“蒋”就是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但毕竟是千百年来的传承,所以后来又恢复了“赶毛狗”的说法。
3、农忙。
作者老家的惯例是种两季稻,中间还插种一季油菜,收割的油菜籽放到油坊,换取每天家里烧菜用的油。“正月的农闲结束,父亲一方面要准备早稻的育秧,一方面要准备油菜的收割。”
作者介绍,其老家早年有一个口号,叫做“不插五一秧”,意思是要在五月一日之前将早稻田的秧苗全部栽下去,这是人民公社时期稍许有点激进的做法。无论是在育秧期间,还是在早稻田的修整,以及田地修整好后的栽秧期间,老家都还是处于春寒料峭之际,世世代代的人们就是这样与天寒地冻搏斗,从严酷的大自然中取得一份可以果腹的食物。
4、端午节。
端午节这一天,作者父亲会采来艾草,插在厨房的门口,同时,要准备雄黄酒,为小孩子涂抹在额头上,据说这样可以驱虫辟邪。雄黄酒有杀菌驱虫解五毒的功效,在没有碘酒之类消毒剂的年代,用雄黄泡酒可以祛毒解痒。
端午节前作者父母还要一起包粽子,到了端午这一天,会把包好的粽子煮熟,剥开后让小孩子蘸着白糖吃,“父亲因为喜欢吃甜食和糯食,这种粽子一顿也能吃好几个。”作者老家的粽子都是素棕(我的老家称素棕为“白米棕”),里面不放任何其他东西。
5、“双抢”。
“双抢”是农村最忙的时候(“双抢”是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不过我那时参加的是生产队集体劳动),是作者全家总动员的时候。这时候一方面要抢收,要把早稻尽快收割并颗粒归仓;一方面还要抢插,要把晚稻的秧苗尽快栽下去。
“双抢”期间每天都在与大自然抢时间,在所有的抢收流程中,作者父亲的工作是关键的环节。“父亲要与我们一起把早稻收割下来,再一起把这些挑到自家的禾场。然后父亲开始犁田、耙田,田地平整后我们再一起下去栽秧,而秧苗又主要是父亲扯回来的,如果秧苗不够,父亲会再去扯秧苗,偶尔母亲也会一起去,留下我和姐姐继续栽秧。”
6、“七月半”。
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也称鬼节,作者老家称为“七月半”,是祭祀祖先的关键节日。如果说春节是人间最盛大的节日,七月半就是阴间最重大的节日。
先要买来黄表纸,然后将这些打过印记的黄表纸放入白色的纸袋,在纸袋上写上祖先的名字,再将纸袋封好,这有点类似于寄邮件,只不过收件人是故去的祖先。“我会协助父亲做一些工作,诸如把打过印的黄表纸放在纸袋里。父亲说不要都放一样的厚薄,要根据亲疏远近来确定纸钱的多少,一般来说是越近的放得越多,越远的放得越少。”
7、“挑堤”。
所谓“挑堤”,就是去给长江干堤及相关堤岸做一些加固的活。这些都是政府组织的无偿劳动,需要自己带好工具,带好米和菜,到离家十多公里远的地方劳动,应该是住在当地人家家里。“后来长江干堤由人工构筑变成机械化构筑的石头护坡堤岸,父亲他们这个挑堤的任务才算结束。”
作者介绍,不仅是挑堤,在农闲的时候组织人们无偿地干一些活,似乎也是其老家这边的通常做法。“我们村有一个湖湾,叫做石湾,是上津湖的一部分。村委会决定在湖湾接近湖中心的地方建一道坝,这样既能方便两岸的来往,还可以把坝内的水域作为村里的自留地,在里面抓鱼、养鱼。这道接近一公里长的土堤也是父亲他们在农闲的时候挑出来的。”
8、过年准备。
为过年做准备工作,作者父母主要做三件事,包括杀年猪、打糍粑和熬麻糖,杀年猪要请专门的师傅(作者老家称为“杀猪佬”),打糍粑也要请好多人一起做,只有熬麻糖是父母两个人的事(麻糖主要用于春节期间招待客人)。
以上8件事的记录对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很有价值。
二、“3”个点(作者成长过程中的关键点)
作者父母对其生活上宠爱有加,但在个人品行上却要求极严,不允许存在任何不良行为。
1、鸭蛋事件。
作者在小学阶段一个暑假的早晨,去湖边钓鱼,看到有几个陌生人在那边用竹席搭棚,同时还有一大群鸭子在湖边叽叽喳喳。他们见作者过去,问他这里是什么县什么公社什么大队,附近是否也有鸭群,他介绍了有关情况。这些人也介绍说是湖南那边生产队里的养鸭人,靠养鸭在生产队挣工分,随着鸭群流浪四方。养鸭人说他们会在这里安营扎寨住上几天,为感谢作者给他们提供的信息,送了几只鸭蛋给作者,还说想吃鸭蛋可以到他们这里来拿。
作者高高兴兴地拿上鸭蛋回家,还在盘算着说不定早晨就可以吃到美味的鸭蛋炒韭菜,这时其父亲回来了。“父亲问我手上的鸭蛋是怎么回事,我说是养鸭人送我的,父亲不太相信,怕我是从养鸭人哪里偷出来的,拉着我来找养鸭人。直到养鸭人说明情况,父亲才放心收下,但回家之后就让我给养鸭人送了好几个鸡蛋过去。”
2、猫咪事件。
作者介绍,他上初中时有同学在上课时赌博,老师在上面讲,几个同学在下面搞小动作,用硬币猜正反来决定输赢。那时大家都没什么钱,玩两次就把手上一点零花钱输掉了。输钱之后想把钱赚回来,但手上没有本钱没法再玩,这时候有同学想到了偷猫。在农村,猫是家家户户必养的动物,不像城市社会猫是宠物,农村家庭的猫甚至可以说是生产工具,就像牛要负责耕地耙地一样,猫要负责防范老鼠偷吃谷仓或者麻袋里的粮食。据说那段时间专门有人在收猫,是要运到广东去,大约一只猫的收购价为五元钱左右。于是,他们班上一帮人就一天到晚在交流哪里有猫、怎么逮猫、如何卖猫。
作者把班上的情况与其父亲说了。“父亲严厉地告诉我,老家的说法是一只猫儿九条命,养儿养女还不尽,就是说猫的命比人还金贵,绝对不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作者按照其父亲的要求,既没有参与赌博,也没有参与关于猫的讨论,后来听说他们班上确实有同学采取了行动,但也因此被养猫人家打过。
3、复读事件。
作者第一次参加高考,比最低录取线差十分,没考上。后复读一年(作者本想去一所学校做代课老师,后来还是选择回母校复读),以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上武汉大学,“当我把录取通知书递给父亲时,父亲将手在裤子上用力地擦了擦,才接过我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百感交集,父亲也是热泪盈眶。”
多年以后作者与朋友交流,说从农村走出来的读书人,其实是大家庭的支持、师长的点拨和个人努力三方面合力的结果,这个大家庭,不仅是自己的原生家庭,而且是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的那个大家庭。作者还特别提到,“如果父亲在我第一年高考后强令我去复读,我也说不定真会去那所学校教书,是父亲对我的尊重与支持让我的人生在关键阶段有了一些转机。”
作者曾与一位同济大学博士毕业的教授一起交流,教授提出的高考理论使人耳目一新。教授说能够考到重点中学的人智力都不差,除了那些特别优秀的,大多数人其实只是完全掌握了所教知识的三分之一,部分掌握了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基本没掌握。教授自己第一年高考没考取,题目应该正好是他没掌握的那三分之一;第二年考了一个中专学校,他没去,题目应该正好是他部分掌握的那三分之一;第三年考了一所比较好的大学,题目应该正好是他完全掌握的那三分之一。“也许我也是像教授一样,第一年正好碰到了我基本没掌握的那三分之一。只是我运气比教授好,第二年就碰到了我完全掌握的那三分之一。”
以上3个关键点,对家庭教育有极大的启示,一是父母应关心爱护孩子,二是父母应严格要求孩子,三是父母应尊重支持孩子。
三、“4”道关(从农村进入城市须面对的考验)
从农村进入城市,必然要面对“4”道关。
1、面对饮食关。
民以食为天。总体而言,作者老家与上海都是江南,所以在主食上没什么差别,都是吃米饭。不像北方人到南方,或是南方人到北方,为了米饭还是面食问题会有很多纠结。但湖北与上海在口味上也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湖北做菜偏辣,上海做菜偏清淡。
“父母到我们家后,尤其是父亲开始掌勺后,父母的口味如何与我们的口味协调,开始成为一件需要沟通的事,父母进入上海城市世界后的饮食关之难开始若隐若现。”口味上的差异还是显形的,在一家人的饮食问题上,还有很多隐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其实还是农村世界与城市世界两种不同文化的映射,以及两种不同经济收入的映射。“父母进入城市世界后的饮食关基本上过去了。这里有农村世界的粗放与城市世界的精细之间的冲突,父亲认同了这种精细的好处,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了这种精细的操作;有不同地域之间口味的差异,我们与父母口味的融合实际上是以父母的迁就为代价的;有不同收入、不同职业间的饮食差异,在这一点上父亲放弃了他原来的收入和职业带给他的影响,而完全站在我们的角度作出取舍。”作者强调,“父母在饮食问题上的认同、放弃、保留以及主动的变化,其实也是社会融合的具体体现。”
作者还谈了这样一段看法(我赞同这一看法):饮食有三层境界。第一层是充饥,以填饱肚子为原则;第二层是美味,已经从物质的充饥发展到精神上的愉悦体验;第三层是享受,饮食只是载体,精神的升华才是主要的。这样看来,其父母原来对饮食的认识是在第一层境界,而上海这边已经进入第二甚至第三层境界。
2、面对衣着关。
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作者上世纪九十年代从武汉到上海读书,到学校后发现有些男同学穿衣服敢于创新,有的人夏天穿衬衫里面不穿背心,冬天会把羊毛衫穿在里面,外面罩上衬衫,再加上西装领带,照样风度翩翩。当时的总体感觉是上海这边的“穿”确实要比武汉时髦一些。
作者曾与一些朋友交流过,他们说“穿”有五层境界,第一层是实用,能解决蔽体和御寒问题;第二层是整洁,穿着干净、整洁,外表平整,没有明显的污迹;第三层是美观,
这涉及到面料、颜色和款式的搭配,也涉及到衣服与个人的身材、体魄相适应;第四层是得体,穿着与自己的年龄、职业、身份相吻合,与不同时间、不同人群、不同场合的氛围相吻合;第五层是象征,穿着体现个人的兴趣爱好,体现个人的喜怒哀乐,体现个人的思想情感,甚至是体现个人的政治表达。
作者父母长期生活在农村世界,在“穿”的境界方面与上海这边还是有明显的差异。当然,其父母除了买菜、送孩子上学和带孩子在小区玩,平时以居家为多,因而在融入上海的穿着关方面几乎没碰到什么大的问题,但也有一点小小的问题。“我们平时回家之后会把外套换掉,换成家里穿的衣服。我们也为父母准备了外面穿的衣服和家里穿的衣服,但父母似乎不太习惯,有时候把家里的衣服穿出去了,有时候回到家里忘了换,多数时候还是以穿外面的衣服为多,尤其是父亲,回到家里马上就要开始洗洗弄弄,我们也没有勉强。”
3、面对交通关。
开门大吉,出行大利。千百年来的农业社会对“出行”是非常重视的,尽管那时的交通工具与现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作者父母到上海后,尤其是其父亲开始买菜,开始送小孩上学后,作者对其父母外出是写了几条规则一直放在父亲口袋里的,基本内容包括外出一定要带好钥匙,走路一定要走人行道,过马路一定要走横道线,过路口一定要红灯停绿灯行,其父母也是严格执行的,除了后来年龄大了有些健忘,偶尔有出门忘带钥匙的情况,其他时候基本都是平安无事。从农村世界走路和骑车的随意性,到城市世界走路和骑车的规范性,从农村世界的地广人稀,到城市世界的车水马龙,其父母过交通关应该说还算顺利,作者认为这可能得益于其父母长期以来的责任心,包括对自己的责任,对子女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
当然,作者说其父母过了交通关,主要还是与其父母的交通方式有关,平时外出以步行为主,有时乘公交车,相对简单的交通出行,让其父母从农村世界进入城市世界后没有出现大的波折。如果是一个在职人员,在上海涉及的交通方式会比这复杂很多,会涉及骑车、开车、乘车的多重规则,过交通关也会艰巨很多。从农村世界到城市世界的人们,要适应快时代的城市交通观念与交通规则确实不容易,但必须学习、了解、认同、遵守,否则就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4、面对医疗关。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人吃五谷杂粮,总有生病的时候。但如何对待生病或者说受伤的同类,却区分着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后,人类先是有巫师,后是有医生来处理各类疾病,尽管这些“巫”和“医”对病人来说并非全然有效,但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平均寿命在不断增长也是不争的事实。
作者父母来上海后,依然在老家缴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险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行,应该也就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但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只有住院才能享受报销,一般的门急诊只能自费。“如果说父母来到城市世界后有什么特别遗憾的事情,那一定是生病就医这件事。父母怕生病后花我们的钱,尽管我们说生病又不是自己想的,就医的费用我们也能承受,但父母依然会为生病就医花费了我们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而自责,为他们在上海的住院治疗花费而感到歉疚。”
作者认为,我们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将农民排除在外的,后来虽然有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其实不论是医疗保障,还是整个社会保障,农民与城镇职工、城镇居民相比较而言,存活在不同的保障体系中。如果两种保障体系是在原来封闭的环境里运行,倒也相安无事,但随着人员的大规模流动,尤其是大批农村的年轻人来到城市就业,这两种保障体系的不相融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即便年轻人在老家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在城市就业后还必须按照规定缴纳“四金”或者“五金”,这样他付出的是双重保险的费用,但在生病就医时却只能享受一份保障。至少在当时,没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城市医疗保障制度之间的衔接方案,这也造成当时城市社保缴费的困境:企业因为增加成本不愿为农村户籍的职工缴纳社保,职工因为没有实际收益也不愿缴纳社保,于是企业与员工达成默契,共同规避社保缴费。
以上4道关的描述和思考,对上海城市治理,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如何快速融入上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四、“1”生情(作者与父母的深厚感情)
全书充满着作者与父母的深厚感情。特别是上大学而离家的那部分描写,感情真挚,让我感同身受。
“真正让我,让父母感到离别的,是我上大学。我们那时考上大学要转粮油关系,还要转户口,也就是从非商品粮转为商品粮,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这就意味着我从法律意义上离开农村、离开家庭了。尽管这个离开是当时大家公认的好事,但离别造成的伤感却从那时起开始如影随形。”
“离家前一天,我挑了两担水,把家里的水缸都装满了。父亲本来说不要我去挑水,但我很坚决,父亲也就没有拦阻。其实,这个活平时都是父亲干的,我也就是客串一下,表示一下我对父母的爱心吧。”
“父亲开始给我准备行李,我们那时候除了要带换洗的衣服,还要带一整套床上用品。我原计划就带高中时的那套被子,但父亲说那套被子他们可以在家里用,我去上大学还是要用新的。父亲用新收的棉花给我弹了一床崭新的棉被,把被套和被里缝好,然后给我打包。为防止弄脏,父亲还在被子外面包了一层塑料布。甚至连打包的绳子父亲都是新买的,说不能用家里的旧绳子,免得被人看不起。”
“离家那天父母起来很早,他们在鸡笼里抓了一只鸡,杀了后把鸡毛褪干净,洗好后切成块,早早地炖在那里,准备作为中午招待客人的主菜。我起来后,母亲煮好鸡蛋,父亲剥好,然后加了糖让我吃。我一下想到这是我小学和初中时生日那天的早餐待遇,高中时住校,生日都是在学校紧张的学习中度过,不可能吃什么特别的东西,父亲在用高规格的早餐来表示对我离家的重视。”
“那天,叔叔和姑妈等一大家子都来为我送行,父亲在那边忙里忙外招待客人,却不忘提醒我要把录取通知书和其他资料带好,把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带好。我告知父亲都已经放在随身带的皮箱里,父亲说身上还要带一点零花钱,又把叔叔、姑妈们送的红包都给了我。”
“我乘当天晚上的轮船去武汉,吃完午饭,父亲就与两位叔叔一起用自行车送我到船码头。老家的船码头于我非常熟悉,因为我的高中母校就在船码头附近,我们经常吃完晚饭后就到船码头那边散步,看着来来往往的船只或者在这里停顿,或者在这里走过路过却错过,不肯为这个小小的港口做短暂的停留。那时我也曾想过,是否这里也是我离开家乡、离开亲人、离开父母的地方,果然,这里成了我走向一个新的世界的起点。”
“随着汽笛声声,我们要乘坐的那班客轮已经抵港,父亲和两位叔叔帮我一起把行李拿到船上,我自己则拿着叔叔送的水果。因为没买到四等舱的铺位票,父亲他们把我送到三楼船尾的大甲板上,父亲似乎还想在船上陪我一会,但船上的广播已经在通知送行的亲友尽快离开,我于是与父亲和两位叔叔道别,催促他们尽快上岸。但父亲临走却又塞给我五元钱,让我晚上在船上吃晚饭,而这五元钱差不多是父母在家一个月的生活支出。”
本书的最后两节是“送别父亲”、“送别母亲”,作者用无尽的思念来追忆父母,让父母永远活在其心里。本书的写作出版,就是其深情追忆父母的较好形式。
作者与父母的“1”生情,充分表达了父(母)慈子孝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是一个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案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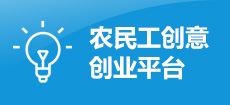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1502003094号
沪公网安备 3101150200309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