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4日,党建研究专家、中国人才研究会理事、华东师范大学党务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行业导师、《组织人事报》原总编辑俞嘉骏主任编辑为李经中理事长的新作《父母的两个世界:一位60后的深情追忆》撰写书评。俞嘉骏总编辑曾担任由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人民网上海频道与《组织人事报》共同主办的上海基层党建创新案例,以及全国党建研究会社区党建创新案例评选专家,也为研究生讲授《组织工作与新闻报道》(组织工作调研报告、党建工作案例分析与写作等)课程。书评标题为“亲情、变迁与融合的微观世界——一位60后读《父母的两个世界:一位60后的深情追忆》”,内容如下:
60后李经中,1987年以全县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1991年,考入复旦大学攻读国际政治系的研究生。毕业后,他在上海市、区两级政府机关都工作过,担任过相关机构的负责人。
在建筑工地挂职时,他下班后会到来自云南、贵州、四川工友的宿舍去,与他们聊天。工友们告诉他,在上海最不习惯的就是饮食,他们干体力活的就是喜欢吃点重口味的大鱼大肉,但食堂里的鱼肉味道清淡。此刻,从农村来到大城市的他,深切地感受到城乡差距带来的理念、习惯、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也唤醒了心中的情怀,必须为像他一样从农村来到上海学习、工作的人群更好、更快地融入上海搭建平台。
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化蛹成蝶后,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组建的社会组织已经成为上海服务新市民的重要平台,他本人也成为移民社会融合领域专家。
岁月如梭, 转眼间,60后的父母大都已青丝染白霜。他们中有的人已驾鹤西去,经中的父母如斯,我的父母如斯。远行的背影,令我们在泪湿眼眶中回首往昔。
在《父母的两个世界:一位60后的深情追忆》这本书中,经中用白描质朴的文字、真挚的情感,记叙了父母从“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世界到随子女迁徙到城市世界的一生。
它是记述文,也是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经中以个人的微观视角,在家长里短、娓娓道来的叙述中,让我们洞见了永恒不变的亲情。
从小学到大学的上学路,是一条充满了绵绵不绝伟大父爱之路。
“到村小学上学,要经过几个沟沟坎坎的地方,雨天路滑,很容易摔跤。父亲在这几个地方用铁锹把一级一级台阶挖出来,上面铺上草和树枝。
中学读书,家里没有自行车,父亲说可以走水路用船送我。怕我睡着了感冒,父亲一路不停地跟我说话。父亲回去时迎着晚风,在幽静得可怕的湖面独自航行近两小时,不知要有多大的动力、多大的毅力才能做到!
到武汉大学上学,父亲他们把我送到三楼船尾的大甲板上,父亲似乎还想在船上陪我一会,但船上的广播已经在通知送行的亲友尽快离开。父亲离开后,我便开始与一帮同学交流,压根没想到回头再看看岸上的父亲。后来父亲告诉我,他们一直在岸上看到轮船远离视线才离开。”
读到此,我想到的是朱自清《背影》中的名场面:“父亲是一个胖子。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60后的父母是最后一代全心全意奉献自己的长辈。
“厨房光线不好,即便是大白天也显得昏暗,母亲先把煤油灯点亮,就着点点的灯光把猪油放进锅里,待猪油融化后,再把饭放进去,随后把煤油灯吹灭,凭感觉在锅里翻炒。待到饭香和猪油的香味都已经浓郁扑鼻,母亲再放点盐,翻炒几下后先尝一下咸淡,觉得可以了再盛好给我吃。
母亲把煤油灯吹灭是因为要节约用油,但母亲为了保证猪油拌饭的质量,还是在关键环节用一下煤油灯。”
上世纪八十年代,考上大学就是“天之骄子”的代名词。60后的父母,大都文化水平不高,我们成了他们的骄傲。
“第二年我以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上武汉大学,当我把录取通知书递给父亲时,父亲将手在裤子上用力的擦了擦,才接过我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百感交集,父亲也是热泪盈眶。”
四十年前,当母亲从工厂下班回家,我把大学录取通知书递给她时,她低下头仔细地看着录取通知书上每一个字。我看到的是,母亲头上的根根白发。此情此景,永生难忘!
经中以个人的微观视角,用一个个日常生活里的父母和家族中亲人的爱、恨、悲伤、命运浮沉的故事,展现了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到本世纪国家的变迁与发展。
60后在农村父母这一代人,是农村社会转型以及中国社会转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一代。诚如书中所言:“他们见证了从成立政治国家以来农村土地上‘皇粮国税’的消亡,见证了自东汉以来代表农村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工具的消亡,见证了千百年来乡土社会家长制以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家庭婚姻关系的消亡,也见证了安土重迁习俗的消亡。”
变迁一:农业税与土地流转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先是取消了农业税,后是对种地实行补贴,按照每亩确定补贴标准。由于国家对粮食实行保护价收购,收入也越来越高。
农村土地流转,舅舅的地都按照村里的统一安排流转出去给企业养龙虾,每年每亩地有近千元的分红收入。”
变迁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从无偿到有偿
“解放以后,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改造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汉以来依靠水车供水的局面,为农业的丰收提供了基本的保障。
等到忙完地里油菜的事,父亲他们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挑堤’,也就是去给长江干堤及相关堤岸做一些维护保养。不仅是挑堤,在农闲的时候组织人们无偿地干一些活,是家乡这边的通常做法。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加大对农村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改造,加强农村公路建设,在资金渠道上由政府购买服务,这时的劳动变成了有偿劳动,按天发放工钱。”
变迁三:社会分工越来越细
马克思认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的表现是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在农村,一个家庭既是生活的联合体,也是生产的联合体,上世纪八十年代包产到户后,这种联合体的特征更加明显。选种、泡种、育秧、扯秧这些活,以及犁田、耙田等重活,都是父亲干,插秧、割谷、挑担这些活父母一起干。扎成一捆一捆的稻谷把从田边挑到打谷场上,家乡称为禾场,要及时用牛拉着石磙,把稻谷碾下来,然后把稻草和稻谷分开,在禾场上晒稻谷,在家门口晒稻草,这些活都需要父母相互配合才能完成。”
“父亲第二次从上海回到老家后,感叹现在种地比以前轻松多了,首先是秧苗有专门的人在做,你只要告诉他需要什么秧苗,需要多少秧苗,何时需要秧苗,别人就会把秧苗送到田边。其次是犁田、耙田、整田、插秧、割谷,也都机械化了。收割机会自动在田地里把稻草和稻谷分开,稻谷也不用自己晒,放在机器里烘一烘,就可以装麻袋保存了。唯一还要人工干的活,大概就是晒稻草了。”
变迁四:农民医疗保障从无到有、不断完善
“很长一段时间,父母看病都是自己花钱。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为父母的生病就医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
国家这几年在异地医疗保障衔接方面确实有了很大改善,也可以说是农村世界的医疗保障与城市世界的医疗保障对接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
父亲在医院住后出院,我去办出院手续时,发现父亲的医疗保障卡竟然可以支付超过总金额四成的费用。”
变迁五:血缘向业缘的过渡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
乡土社会的基础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核心是血缘和亲缘关系,而血缘和亲缘关系的存在是以庞大的家族网络为基础的,在这个网络之中,大家相互帮助、相互支撑。
“解放后划成分,以外公当时的家境和每年要雇短工甚至还有长工的情况,有人建议划定为富农成分。但外公雇佣的都是自己本家的弟兄,对待他们也是像亲人一样,这些弟兄也都帮助在工作组那边说外公的好话。当时工作组的负责人姓颜,据说孔、孟、颜、曾四家因为孔子的关系都算是本家,所以姓颜的负责人就照顾了姓曾的外公,将外公划定为中农。”
“姐姐十四五岁时,有一天突然站不起来。父亲很是着急,去找了二叔和三叔,应该也还有表哥,三辆自行车载着姐姐、父亲和行李去医院;向生活条件稍好的亲人借钱也是常有的事。”
“古代中国的婚姻,除了五服之内的同姓不能结婚,什么姑表亲、姨表亲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大姑妈嫁给了自己的表哥,也就是自己姑妈的儿子。”
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小家庭,让乡土社会一个一个庞大的家族网络瓦解,也让熟人社会失去了基础。一批一批的农村人,离开熟人社会转向城市的陌生人社会。
“吃完年夜饭,休息一会后,父亲会带我们去祖宗的坟地送灯,据说是要用灯照亮祖宗回家的路。这送灯与其说是一场祭祀活动,还不如说是一场社交秀。
在同一时间去送灯,这里能碰见许多多年未见的乡邻。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家乡人奔赴四面八方去谋生,西边的新疆,东边的上海,南边的广东,北边的北京,都有家乡人辛勤劳作的身影。”
“2019 年元旦前夕,二姑父的孙子盼盼在上海附近买的房子装修完毕,盼盼把二姑妈、三姑妈以及二姑妈家的几乎全部亲人都接到了上海。这时候父母也在上海,加上早已经在上海的四姑妈一家,我们一大家子在父亲住地附近的酒店聚会。这次聚会的规模算是空前绝后的,从人数上来看有接近三十人。”
变迁六:移动互联技术与传统的身份秩序同时并存
移动互联时代的农村社会,最现代的东西与最传统的东西奇妙的组合在一起,微信和支付宝与传统的身份秩序同时并存,既让人感叹传统的伟力,又让人感叹现代技术的渗透力。
“有个女孩子一直在忙活着打印字条,这是家乡殡葬一条龙的一部分,有专门的人员在从事花圈和花篮的事务。吊唁的人只需要告知姓名及与逝者的关系,他们便会将信息输入简易打印机,将打出来的字幅挂在花圈和花篮上,一幅定制的花圈和花篮便可完成。一个花圈二十元、花篮二十元,收款都是支付宝或者微信,非常方便。
听到外面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随后又是唱歌的声音,登弟告诉我不必出来,是那些‘文乞’到了。这些人是有组织的,来到门口的只有两个人,还有两个人在车上,敲锣打鼓的就是车上的人,露面的是女人,在车上不露面的是男人。一般行情是按四人给,每人二十元小费加两包烟,算上去每人就是七十元左右。按行情给就行,不能给多,给多的话这些人也是有微信群的,一个定位一发,一会儿就会有好几批人来接受丧家的慷慨发放,且都是开车过来的。”
60后的农村父辈,来到城市世界,面对的是制度、文化与观念方面的种种差异。经中以个人的微观视角,描述了父辈通过认同、放弃、保留的痛苦过程,在新旧两个时代交汇过程中,在碰撞中找到了融合的路径。
文明相对的是野蛮,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实现文明的方式与手段,不尽相同,这就是文化。个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逐渐习得自己所处社会的风俗、习惯、语言、价值观,掌握知识、技能,得以融入社会。
脸朝黄土,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背朝天,是身后未知的世界。
古代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科学技术不发达,许多自然现象无法用科学解释。破解背朝天这个身后的未知世界,依靠的是迷信、神话传说、民间故事。
“按照父母的说法,家里的一切物品,都有相应的神祗在掌管,如喝水用的水瓢有瓢神,吃饭用的筷子有筷子神,饭碗也有碗神,烧饭用的炉灶有灶神。实际上,‘请瓢神’是人们希望新的一年风调雨顺。
在城市世界,当母亲遇到疑惑的时候,再也不能向她的神灵求助,因为家里没有地方可以焚香烧纸。但母亲还是慢慢的适应了这种生活,在母亲膜拜的那些神仙的生日,母亲会对那些神仙说现在不能焚香,等以后回老家多点一些香,把这几年欠的补回来。”
从农村来到城市世界的父母,那些长期以来支撑他们的信仰体系,在与城市文化的碰撞中也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我们还带父母去过老家的寺庙,求菩萨保佑不要晕车,似乎依然没有效果,那天父母拜完菩萨回来就在车上吐得一塌糊涂,但这一点也不影响父母对菩萨的信仰。父母对此的解释是:那么多人都去求菩萨,菩萨怎能一个一个都照顾得过来呢。”
城市与农村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各自不同的社会化历程及文化熏陶,造成人的衣食住行习惯大不相同。60后在农村的父辈们,在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中,通过碰撞、痛苦、放弃与部分保留,逐渐融入城市世界。
“农村世界的公路是没有红绿灯的,直到现在老家镇上也只有一个红绿灯路口。除了大家心目中隐隐约约有行人靠右的意识之外,农村世界的行走基本上是随意的,与交通相关的规则是缺失的。
父母从老家来到城市世界后,我最担心的就是交通安全问题。坐小汽车,应该是父母进入城市世界后的第一关。父母到上海,我叫了出租车,但父母上车一会儿就开始晕车,我赶忙拿出准备好的塑料袋,让父母吐在塑料袋里。”
“老家盛菜的碗大,菜的量也足,一方面与蔬菜是自己菜园里种的菜,不需要花钱有关;另一方面,在老家干的是体力活,自然胃口也会好一些。在上海的家里做菜,是讲究品种要丰富一些,而且最好一顿或者最多一天要吃光,这样每次菜的量就不能太大。父亲也慢慢明白了其中的差别,做的菜品种多了,但每个菜量都少了。”
2024年9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5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2023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6.16%,比1949年末提高55.52个百分点。
按照统计推算,1949年前的中国人口城镇化率仅在10%左右。可以说,出版于1947年的《乡土中国》,对以农村为主要特征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费孝通先生做出了极为深刻、经典的剖析。
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社会城镇化特征已非常明显。在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城乡融合的大背景下,传统中国乡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成为这一时期的题中应有之义。经中以个人的微观视角,为我们近距离观察这一冲突与融合,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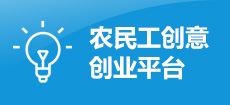
 沪公网安备 31011502003094号
沪公网安备 31011502003094号